“忆”与“望 ”中的乡愁路
□许瀚丹
记忆中的“山景房”
提及故乡,我眼前浮现的是一幢楼。它坐落在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那市区与郊区的交界处,是我度过童年的地方。那幢楼有九层,没有电梯,家住七楼的我回家时总是气喘吁吁地打开家门。那是我见过的视野最开阔、景色最大气的一栋楼房——一栋“山景房”。我还记得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一幅很壮阔的画面:下面是几块农田和几间农舍,时常可见农夫行走田头、浇水除草的身影;远处近似一片荒野,焦黄墨绿浅褐等颜色交织着向远方绵延;最远处,是两座大山,从山脚到山顶,完完整整的收入眼底。我无法看清山上的草木,甚至无法辨别山的颜色,但我可以看到它们完整的形态,威严的气势,以及泰然不动的沉稳。
阳台是朝东的,每个早晨,红彤彤的太阳都会在山顶露出半张脸,再在跳出另一半脸蛋时带来刺眼的万丈光芒。而许多夜晚,月亮也会羞涩而娴静地慢慢爬上山头。每月农历十五,尤其是每年中秋,我和家人不是守在客厅的电视机前,而是站在阳台上,静静地等那玉盘般的圆月映入眼帘,洒下清辉。月亮当主角的夜晚里,山和荒野,成了最好最美的背景。
初二时我离开那里搬家到市中心。新的房子更大更美,只可惜开窗就是另一幢楼房,唯一能瞥见的“外景”,便是整洁的柏油路和川流不息的汽车。中秋节,吃着香甜的月饼,看着精彩的晚会,却在听到“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的歌时忆到了那栋老房子,那两座山,还有那些真正看月亮爬上山头的时光。
听“山音”响起来
妈妈是重庆人。在山城的农村长大的她,永远记得那些走山路、捡山柴、唱山歌的日子。在大山里,不见人影,只闻人声,人为和自然的旋律交织在一起,成为妈妈脑中独特的“山音”记忆。
攀枝花的山也不少,举目四望,穿过参差不齐的高楼,便能看见连绵不绝的山峰。市中心的公园就是以一座山为主体修建的。公园通过上下坡与石梯的道路引导游人完成山脚与山顶间的转换,在中间的平缓地带是游乐设施,山顶处还有观景的亭台。而路两旁是未加开发的树林与山坡,走在其中,真的有行在山间的感觉。公园建成后,我和父母都很喜欢去那里散步,走在夹有水泥路的山中,听风掠过树梢,听鸟儿在林间鸣叫,听不知何处之人在山中歌唱或长啸。每当这些“山音”响起,妈妈的脸上,总会现出回忆与满足的笑容。我想是这里的景、这里的音,让她的乡愁有了着落与归宿。
让乡愁留下来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假期去走亲戚,小表弟在宽敞舒适的房间里,吃着苹果,无精打采地读着要求背诵的诗歌。从他的声音中,找不到一丝“乡愁”的味道。我不禁想:我自己的乡愁已经很淡了,那我的下一代及其后人,生活在日益相同的城市里,他们还会对故乡有感觉吗?
似乎没有人可以阻止城市规模的扩张,就像没有人可以阻止历史前进的脚步。然而在华灯早已亮过星星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努力留住另一种浓烈稠密、萦绕不绝的东西——乡愁。那是一条于每个人都不同的道路,偶然一走,便能从自己脑中的过去,走向心中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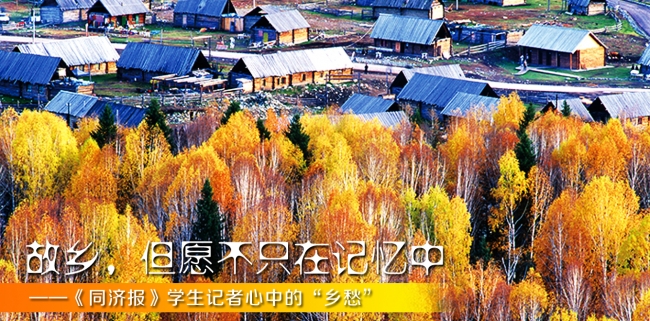
邂逅一片油菜花田
□谢文欣
前几天收到了妈妈的一条微信,打开一看,是一张爸爸的照片。他站在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田前,身子微弯,把脸凑到油菜花边,对着镜头露出一个略孩子气的灿烂笑容。附上了妈妈的一条解说:“今天我和你爸开车去看油菜花了。”心下立刻变得暖融融的,会心一笑后想起了很多年前的往事,在我还很年幼的时候,一家人在初春的季节,也会趁着春日好时光,到成都的郊区去踏春赏花。可能是三圣的桃花,龙泉的梨花,或者也可能是在城郊某个说不出名字的地方偶遇一片金黄盛开的油菜花。我并不十分在意花是否名贵美丽,只是单纯喜爱那种生机勃勃的活力,只是享受那种和家人在一起的温暖。而今我一人身在他乡,看到此景更是无比唏嘘怀念。
离家的游子对故乡的变化总是敏感的,上一个假期回去,熟悉的春熙路上半年前还在修建中的地方,一座摩天大厦已经拔地而起。一只石雕的熊猫攀爬在大楼身侧,憨态可掬。短短半年,我熟悉的故乡已经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日新月异了。但是细细想来,难道不是从我还是一个呀呀学语的稚儿的时候开始,我亲爱的家乡就已经在岁月更替中悄悄地飞速改变了吗?我三岁时曾嬉戏过的天府广场,现在已建起了美丽的音乐喷泉;我初中学校旁的水井坊酒厂,现在已翻新重建,陈列了一个水井坊博物馆;我高三时偷偷跑出去玩的小镇,现在已经被定位成下一个市中心;我家门前老旧的公交站,现在也变成了明亮崭新的地铁站。
又有太多的东西是没有改变的,它们一直停留在这里守护着这片土地。广场改造了,但是在广场中共享天伦的欢声笑语不曾改变;酒厂翻新了,但是在小巷中久久弥漫的浓浓酒香不曾改变;小镇创新了,但是小镇中人们质朴友善的品质不曾改变;公交革新了,但是在车上人们为老人让座的行为不曾改变;成都的城镇化在飞速推进着,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城郊邂逅一片美丽的油菜花田。不论城市怎么发展,成都人依旧如旧时光中的成都人,在周末的下午,倦懒地晒着太阳在茶馆里打牌聊天。
还想起假期时,发烧友的舅舅兴奋地给我们展示他收藏的“老玩意儿”。“玩的这个东西呀,你们现在肯定在哪里都找不到了!”舅舅指着他收藏的老唱片机得意地对我们说。“我现在已经把你外公外婆家完全布置成70年代的样子了,老电视,收音机,缝纫机。过两天,我准备去成都的老电器市场逛逛,再淘一个胶片放映机回来,到时候给你们放《小花》!”他的眼里闪烁着耀眼的光彩。
我觉得我似乎也开始怀旧了,怀念在春风的三月里,和家人一起去踏一场青,邂逅一片金色的油菜花田。也许等到放假回家时,春已经过去了,不过正好我可以和爸妈一起去一次青城山,那里正是个夏日纳凉好去处。
从泥沙到金沙
□胡贝妮
我生活在金山已经二十多年了,从小到大,楼房拆了又建,学校搬了又造,唯一没有变动的是那片大海。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岁月如何蹉跎,海一直在那里,潮起潮退。
翻开泛黄的相册,和大海合影的似乎特别多。小时候,妈妈总喜欢抱着我去海边玩耍。而童年时候的我好像对大海有着深深地恐惧,一在海浪较大的地方就会哭鼻子,许多照片都是带着一张苦瓜脸、躲在妈妈的怀里。长大后,和同学开玩笑说:“上海城区孩子的童年都会有一张人民广场喂鸽子的照片,而金山孩子的童年都会有一张和大海合影的照片。”的确,那片大海承载着每一个金山人的生活,从出生到终老,见证了无数个春秋的变迁。
记忆中,那时候的海水黄黄的,远处打来的海浪泛着若隐若现的黄色;那时候的海滩还称不上沙滩,只有黑黑的、粗糙的泥沙;那时候的小孩喜欢在海边放风筝,喜欢在黑黑的泥里挖螃蟹;那时候的大人喜欢在海里游泳,享受海浪席卷而来的快感。说到那黑黑的泥沙,小时候的我最喜欢做的就是脱去鞋袜,赤脚走在上面,脚底感觉细细的,硬硬的。时不时的会有小螃蟹从小洞里钻出来,用它小小的钳子碰触我的脚底。
长大之后,对于大海的记忆逐渐模糊,去海边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对大片海的重新认识来源于一幅壁画。在上海的欢乐谷有一幅壁画,画上是金山城市沙滩的新面貌:波浪形的长廊、金灿灿的沙滩、蔚蓝的大海……这幅画勾起了我对于那片海的好奇。
在空闲时间,我去了那片记忆中的大海。那里有了摩天轮、海上摩托艇等娱乐设施;大海被围起来了一块,海水变成了蓝色;从前那黑黑的泥沙变成了金灿灿的沙子。依旧脱去鞋袜,赤脚走在上面,脚底感觉热热的,软软的,每走一步,都会留下一个脚印。旁边的孩子正在玩着沙,堆着他们想象中的城堡。情侣会牵着手在沙滩边漫步。爱好运动的男人们戴着墨镜,在沙滩上踢足球、打排球。这是一片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海,这是一幅我从未见过的画面,更加现代化,更加富有活力。
在依托这片大海推动城市化的同时,金山还保留了上海最后一个渔村。在金山嘴渔村,依旧保留了白墙黑瓦、小桥流水的江南古巷。站在那里的码头,依旧可以看到最真实的杭州湾。那片海,依旧是黄黄的海水、黑黑的泥沙、海浪翻滚、波涛汹涌。依旧有早出打渔的渔民,摇摇晃晃的捕鱼小舟,归来时的满船海鲜。浓浓的金山原来的风味在这里得以保留,那一代代人的乡愁啊,终究没有消散……
(题图摄影:张晨曦)